苏格拉图对话:这是一场全有全无的博弈
这是一场一位中年人(下以“苏格”戏称)与一位年轻人(下以“拉图”戏称) 的对话,很有跳跃性,从政治,到传统,到自我,到攀比,到宗教,到爱情,再到血气,到教育,等等,诸如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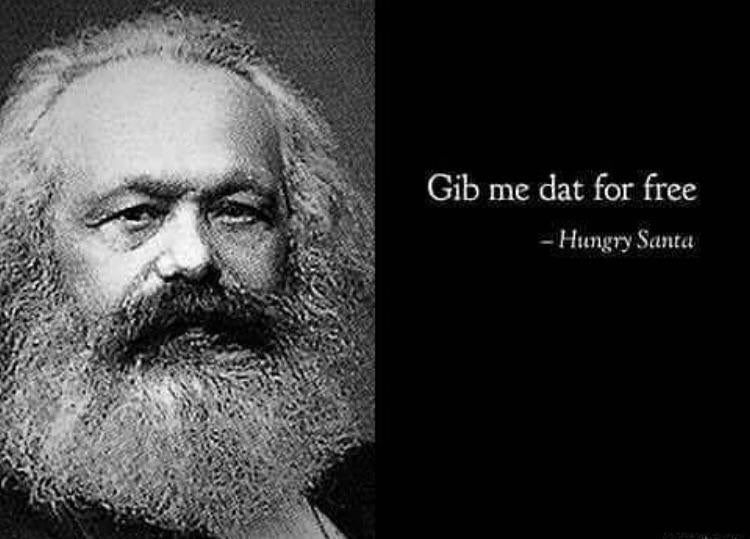
拉图:早晚的事情。堵不如疏,越堵越积越重,喷发而出,代价越大。他们咋就不清楚呢,还是说结构性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要回到根本的问题上,那是他们最恐惧的事情。
苏格:结构性问题。这是一场“全有-全无”博弈。十二年前我就看清了这一点,这也推动着我这些年来无法不去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必须破解它,超越它。
拉图:可以解釋一下嗎?
苏格:首先,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两个基本点”,你中无我,我中无你。你退一尺,对方进一丈,这才是中国社会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或者说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其次,儒家“家天下”和“利出一孔”的惯性下,一切问题都会争权夺利,动一条桌子腿都会流血,内斗,毫无底线和约束。结果只能是紧抓权力。政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无法建立有安全可保障的信任关系,这是根本问题。中国人之间的安全、契约和“信任”是靠单一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来保障的,这也就是他律性和外生性,但是,政治领域内却没有在其之上的更大的外部力量来约束和保障政治领域内的契约和信任关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拉图:我最近對這個事情感觸很深。
苏格:近现代过程中,西方政治领域的信任关系的保障,其实是有宗教信念和教团的软性力量来支持的。但中国没有这种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国共重庆谈判必然会破裂的根本原因。政治领域中,出尔反尔是常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袁世凯称帝前,下属大佬们都表示支持。但称帝后,那些大佬纷纷倒戈。这种政治生态你是没办法的。
从这种对比,我们可以提炼出一点,即任何真正的关系,其实,不是一个二方关系,而必须是一个三方关系,比如说,在“你”和“我”之上的一种共同的东西是“你”和“我”建立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且,这种关系要是想稳定且持久,那就需要最终在上的“第三方”是虚的而不是实的,比如说某种信仰而不是某种权力实体,例如,爱情只会发生在相信爱情的人之间,只要有一方不相信,或企图想以权力或金钱来替换,那爱情也将变得不可能。在西方文化中,这个第三方曾经是上帝,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我看来,这个第三方大体上来说,是缺失的,或不怎么有效的,要么是“空”的(佛),要么是杂的(道),要么是实的(儒)。
拉图:他們沒有辦法想像,不是出于利益,人和人之間的聯繫怎麼可以那麼親密,即使是社團和宗教他們也能歸為利益。您覺得您的新的“三位一體”(自尊-创造-爱)理念,或者說是信念的轉換,可以“改造”我們嗎? 我現在也不清楚有沒有一個最好的社會結構,政治體制,人機模式,目前所知道的,最好就是您提出來的以那個三位一體為基礎所建立的了。
苏格:我所设想的“自尊-创造-爱”的三体结构,是为了替代一直在起作用的“权力-金钱-性”而提出来的。我这几年切身体会到的是思想的边界约束,一是,它只会对极少数人才有效和吸引力,二是,这恐怕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
现在最大的理论难题,依然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上已经失败了,其实,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行的,那就得重新寻出路。这个三位一体面临的挑战是,多数人会为了吃饱饭或舒适一点,而宁愿放弃尊严、爱与创造。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一条刚性原理。它对应的正是目前正流行的概念“无条件社会基本收入”制度。这是原理与现实政策的一个对接。只有在这一条满足之后,人性(human nature)才有可能会健康饱满地生长,自然潜能才会变成社会现实。这是美好世界的一个必要条件。
拉图:是的,尊嚴是要付出代價的,愛是要付出精力的,創造沒有剽竊更吸引人。
苏格:一个人选择创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能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即便能创造出来,时间周期也是不可知的,不可控的,猴年马月的事儿了。所以,很多人要么选择常规,按部就班,要么选择剽窃,投机取巧。创造和创新,迄今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所谓例外,就是有挺多机缘巧合的因素在里面。也是不可复制的。要想人类社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创新,那起码一条,就是必须要从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做起。
拉图:是的,現在我們可能面臨著,連基本收入有些人可能都喪失了來源。
苏格:所以,“地摊经济”来了。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政治领域的常态,必然也会反射到治理政策上。
拉图:受害的還是百姓,但是百姓的冷漠還是百姓承擔,這個結構難破呀。
苏格:是的。需要外在力量,但这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拉图:破題者還是自身。
苏格:百多年来的中国,不也是被外来的力量殖民和蹂躏嘛。最终还是得思想观念上的,虽然有限,缓慢,但是必需的,不可或缺的。我常回想自己的改变,首先当然是思想上的开窍、观念上的改变为先导的。
拉图:思想上的改變的前提是要,可以聽見跟自己原來的觀念,不同的觀念。可以就與自己相處的觀念進行辨析,然後才能讓自己明事理呀。現在這份土壤也變質了。但是並不悲觀,可以改變自身的土壤嘛。
苏格:我不相信国人都是蠢货。一方面,只是现在理智一点的声音被压制下去罢了,另一方面,一帮雇佣水军和自媒体在兴风作浪,乘风破浪,前浪后浪。这与真实的社会心态是不成比例的,千万不要以媒体和舆论来判断世界。当然了,我也不会高估中国社会的心智状态。一切认识、知识最终都可溯源于比较,但国人呢,把“比较”变成了“攀比”,各种羡慕嫉妒恨,戴着歧视链行走,这就把客观和逻辑范畴,转换成了主观和心理范畴,自然就会越来越狭隘和愚蠢。哈哈,很悲剧。
拉图:學術圈攀比之風。
苏格:哪个圈都在攀比。
拉图:目的已經不是人本身了。
苏格:一个人一辈子,衣食无忧,有自尊,有爱情,有创作。我认为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间就是值得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认为美好的社会创造出来。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是没有“人”,没有“自我”的,而佛教又将“自我”给虚无化了。例如,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包括皇帝在内,正是一个个“宁作我”而不能的状态。鲁迅先生也早说过了,“吃人”的礼教。
拉图:兩個文化剛好,把自我弄沒了,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找到“自我”嗎?
苏格:自我不是实体,而是通过一种与世界建立一种善良、诚实和单纯的关系的过程中的创造和构建。所以,自我是一种行动。一种善良、诚实和单纯的行动。
拉图:我現在相信一句話,祇有先建立“人類之城”,“上帝之城”才能建造。人在上帝之前,所以人本身是目的,所以自我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您覺得呢?
苏格:是的。关于宗教与上帝,我当然也思考过。因为这是绕不过的问题。我的策略是,把顺序颠倒过来,如你说的一样。从人出发,建立从人出发而不是从上帝出发的基石。关于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争执,我还是持中间立场:上帝存在与否,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争论这个问题是无谓的。建立以人为本的美好世界,先把今生今世活好。至于死后,有神则更好——自尊、创造与爱的人格和体验至少会有进入“上帝之城”的优先权吧。没有神也无妨。
拉图:這樣的話,可以達成人和上帝衝突的某種調和。很多宗教都是向善的,他們將神這個大他者放進人類的世界,有一部分目的也是為了讓人向善吧?
苏格:是的。有好的方面,这毋庸置疑,但也会被坏的利用,是把双刃剑。谁在利用呢,归根结底还是人。所以,首先还是得解决“人”的问题。
這些東西無不是息息相關的,但是他的根兒還在於人,人的根兒在於自我。這樣就串起來,而自我的根儿,在于亲子关系,在于爱或不爱。在于爱与智慧。
拉图:愛原來如此重要,俺還沒有談過戀愛,還意識不到。
苏格:只有在爱中,自我才不至于掉进自我中心的旋涡。现在的人们,不正是自我意识过度膨胀嘛,变成了自恋主义和自我至上主义(人与人的攀比)。现在的那些所谓“佛系青年”,其实只是这种形式的衰弱和贫乏版本,其实并没有从“自我”(ego)中走出来。“佛系”只是对无能的自我的一种自我合理化方式。
拉图:嗯的。我之前看《愛慾之死》的時候,雖然可以理解那些文字,但是並不是能十分深刻的認識到。我理論說的一條一條的,但這不是智慧。
苏格:美好的自我的根在于美好的亲子(子亲)关系;美好的亲子关系的根又在美好的夫妻关系,又在于美好的爱情。而美好的爱情,在于社会能够不断在养育和教育出“美好的个人”(自我)、“最可爱的人”和“爱的主体”。
拉图:社會又是由人構成,一個閉環形成了。
苏格:哈哈。智慧是包含体验的内容的。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经常性“缺智”(intellect),又没“智慧”(wisdom),即塔勒布所说的IYI(intelluctual yet idiot),关键还是缺乏相应的体验结构,真的是成了纸上谈兵的“读书人”。这造成了身心的分裂、行动与思维的脱节。
拉图:體驗的缺位,這個真難受呀。
苏格:还是尽可能地多参与一些社会公共活动,尤其是那些非功利性的活动,有机会做做义工也不错。在这样的场合发生非功利性的交往的概率也相对比较大一些,未必不会遇到真正的友谊与爱情哦。当然,由于这都是不可预期的,不可算计的。所以,即便脑中有时闪过这样的念头,也不可视为“功利主义”,因为,渴望友谊与爱情是人的自然本能,而且,在真正的友谊与爱情中,人们做的更多的其实是“付出”而不是“得到”。
拉图:這倒提醒我了,千萬不能只做個書呆子。
苏格:年轻时,少读书,多做事。先别读那些自己消化不了的书。这跟吃饭是一样的。要对一些领域保持“理性的无知”。别忘了,多运动,提升血气。我第一次看到川普照片时,觉得他是一个有血气的人。我从来不会小看一个有血气的人。大多数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大多是缺乏血气的,不值得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拉图:這一點我現在可以認識到了,您這麼說了之後,我回到學校之後也在運動。我可以感知到,那種就像您說的有血氣和無血氣,兩者的區別是多麼的巨大。而且有血氣的人,怎麼樣也不會向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妥協。非常感謝您的再次提醒。之前我一直在想怎麼樣去突破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現在我才知道,原來一個很關鍵的點在於血氣。
苏格:嗯是的。有血气的人,不会人云亦云的,不会轻易认输的,也不会急于给自己一个自欺欺人的答案,至少会自己去寻找。但现代教育体制对学生的血气是阉割性的。有血气的人,会很在乎内心的尊严(而不是外在的所谓“体面”),有强烈的自尊心。
拉图:那個尊嚴和自尊是自己給的,自己爭取的。而不是以一種符號的方式,跟其他的符號進行連接。
苏格:是的,是以真实的关系的方式。
拉图:他們有著自尊和尊嚴的基礎,所以他們會很有底氣,內心也就相應的強大,他們也就可以更好的面對挫折和挑戰。
苏格:嗯,是的。
拉图:而血氣不正之人,精神必萎靡,若遇艱難跟挑戰,放棄是常態。之前所盛行的佛系,是不是可以看成一種血氣缺失的症候?
苏格:是的。这是必然的。佛系只是一种自我合理化的话术。
拉图:有這種傾向,我覺得血氣不正之人,是統治者最想看見的。他們面對生活便已經用盡了全力,生活之外的訴求,顯然可以置之身外了。
苏格:是的。所以,不要低估中世纪的文化残毒和政治残毒。什么是“中世纪”?中世纪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儒家的“克己复礼”,要驯服的就是人的血气。西方的基督教也是在驯服血气。
拉图:都有要服從的東西。
苏格:因为,血气有两个方向,一是哲人,一是僭主。东西方文明都在驯服僭主。防止僭主,也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消灭那些有潜力进行篡位夺权、取而代之的人。驯服你的血气,打断你的脊梁,磨平你的反骨,你也就没有那个“潜力”了。
拉图:嗯嗯。
苏格:这个很明显。可以看看这本书,《血气与政治》。
拉图:見識了,還有一本書,講這個問題。我突然想到了一句,這個時代只生產馴服的肉體,今天您這麼一説,細思極恐。
苏格:因为从肉体到精神,中间环节就是血气。在古希腊哲学中,灵魂分为三个部分,嗜欲,血气,nous。血气就是通过精神的梯子。Thumos (also commonly spelled thymos; Greek: θυμός) is a Greek word expressing the concept of "spiritedness" (as in "spirited stallion" or "spirited debate"). The word indicates a physical association with breath or blood and is also used to express the human desire for recognition. It is not a somatic feeling, as nausea and giddiness are.(来自wikipedia)
拉图:嗯嗯。之前看過一篇文章,講的就是國家如何控制人的強壯身體以振精神,來最終達到控制人的目的。血氣方剛是一種最佳的狀態嗎?
苏格:当然不错。其对立面就是力不从心。血气,受到压抑,阻断,爱欲也就受到抑制。性与爱都会得不到美好的满足。便会造成一系列的或隐或现的心理和身体症候,而这会进一步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犯罪问题。
拉图:身邊的人有這樣的,那麼重振血氣,除了運動之外還有別的方法嗎?
苏格:运动首先在于“疏”,把此前堵塞的状态打开,疏通,但关键还是在于信念,以及认知、理性和意志的提升。例如,对于专注力、想象力和意志力的训练。
拉图:嗯嗯,原來是這樣的,之前我還以為祇有我身體上的呢。
苏格:有了血气,还得向有意义的而不是攀比的方向集中和聚焦,这就需要理性、判断力和意志力,这样就会得到正反馈,不断加强,不然也依然是问题。Plato depicts logos as a charioteer driving the two horses eros and thumos (erotic love and spiritedness are to be guided by logos)(来自wikipedia)。
拉图:確實,理性引導的嗎?
苏格:有理性,也有直觉。只有你一直保有血气,且心持善良、诚实和单纯,你就会被引向正确的地方,尽管中间不可避免会跌跌撞撞,“吃一堑,长一智”。
拉图:也就能把握各種大事和小事了吧。
苏格:是的,也可以这么说。血气之上的Nous,恰恰正是一种全局观的能力,全局性的把握能力。血气匮乏的人,也一般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拉图:那應該就不至於犯很大的錯誤了,但是這樣做的話,代價是一種要持續承擔的存在。
苏格:自然是的。但一般不会犯战略上的错误。有战略能力的人是必有血气的。虽然反之未必成立。当下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有血气的人手里。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charisma)的人物手里。学院型知识分子,也就是塔勒布说的IYI,会成为秋风下的落叶。我很明白川普他的局限甚至是狭隘所在,不是一个能够超越既有的资本主义结构和引领未来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敢于打破幼稚又虚伪的“政治正确”而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有血气,接地气,更像是军人,而不仅仅是商人。国内那些蠢货,仅仅把川普当作商人,是一个巨大的误判,战略误判。商人,以“利差”为食,属于缺乏血气的人,因为国人基本上都是“商人”(文人也是商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就只能看见什么,所以看不懂川普。以国人那种狭隘的商人观念去套川普,肯定是驴唇不对马嘴,大错特错的。误判川普的人大多是所谓的学院知识分子(IYI)、媒体人,以及一些易受这些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影响的学生群体。
拉图:您可以說說您是怎麼看待川普的嗎?
苏格:这个以后再说吧,我可能会写文章。
拉图:期待下。
苏格:一直感到很悲哀的是,在重要问题上,这些年,居然我就没看到一位足以让我佩服的头脑。哎,太悲哀了。我说的是在思想和知识领域的分析认识上。
拉图:我之前也聽過類似的說法,他們說這是個哲學家,不出世的年代。唉,哲學遭遇了它本身的危機。
苏格:大多被认为有一些见识的,也只是流于表面。
拉图:對了,您可以談一談您對哲學危機的認識嗎?
苏格:简单地说,就是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是自上而下的,未脱离神话和神学的残余,造成了“两个世界”(柏拉图)的分裂,只有本体论(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再加一点不完整的认识论,而一直未能完成主体论的构建。我的哲学观是,哲学应该是三位一体的螺旋线:本体论-认识论-主体论。本体论的意义就是,要回到事物本身;主体论的意义就是,要回到人本身,这必然会引发人性的认知问题。这是最难的,也就是康德在提出“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之后,不得不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人性是什么?
拉图:遺忘的哲學史是一部主體的遺忘的歷史,胡塞爾的現象學有沒有解決本體論的問題啊?
苏格:主体论,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自我,以及亲子关系,爱情关系,家族关系,以及整个闭环。这在迄今为止的哲学中是鲜有讨论的。所以可以说,当然没有。
拉图:我發現愛情好像在整個哲學體系裡面不是很受待見。
苏格: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哲学本体论,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啊。这可能与哲学家大多是单身汉有关吧。哈哈。
拉图:好像還有幾個哲學家有厭女情緒。
苏格:这个世界的主要思想,是由“出世”的人主导了。这是不正常的。
拉图:好像似乎我還不知道有一對哲學家夫妻的,我現在跟以前一個很大的轉變,就是我完全不是很倡導“出世”了。
苏格:著名的哲学情侣是萨特和波伏娃,但他们都是携带着某种程度的厌世情绪吧。。。
拉图:哦,好像僅限於他倆了,好像還有海德格爾和阿倫特。
苏格:嗯。海德格尔谈死,向死而生,但爱(love)或爱欲(Eros)不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那么,这就依然没有跳出西方古典哲学的“哲学即练习死亡”的框架,而在古希腊的诸神退场、基督教的“上帝死了”之后,这样的现代的练习“向死而生”的“此在者”,实际上,并不能克服虚无主义的四面楚歌。所以,我怀疑海德格尔哲学深渊中本身就隐含着纳粹主义的恶龙。
拉图:我記得海德格爾好像把情緒拉扯進了哲學裡。我最近聽到一句話,特別有感觸:愛情是死生中最長的一瞥,最近越來越感覺到重要了。
苏格:死的对立面不是生,而是爱。
拉图:因愛而生嗎?
苏格:严格说,死并不外在于生,而是内在于生。这也就是“向死而生”的意义。而在这种死亡意识的张力和理性之下,导向人生之意义的则是爱和创造。向死而爱。死和爱,是生的内容。
拉图:嗯嗯。
苏格:死和爱,如阴阳鱼,正是在死和爱的纠缠和张力之中,生之意识才会活着,有活力,有精神,有献身。
拉图:死是每個人固有之,但是愛卻不一定。
苏格:是的。但是,爱却是每个人渴望之。它一直在起作用。所以,它就像是复数的虚部一样。爱,是一种梦想,理想,想象,“未来”,每个人总是希望把爱的潜能变成现实,就像一颗种子“渴望”自身变成果实。
拉图:缺少了虛部,它就不是复數了,就變成了實數了。
苏格:是的。现实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实用主义者,都是实数。也包括那些“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跑道主义者,但这就跟点只是在线段上移动或跑动一样。
拉图:還可以這麼看哎,我第1次見到有人用數學來看待社會的。
苏格: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方向和可能。虚部就是负责旋转方向的嘛,对吧。
拉图:是的,是的。
苏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是如实数那样。应试教育就是把所有的人变成实数,是不是。
拉图:是的,讓人遺忘掉,還有虛部的部分可以使自己發生轉變。
苏格:让你没有理想,没有想象力。请注意:复数z=a+ib中的虚部i的英文是怎么写的,imaginary。
拉图:那這麼說的話,單向度的人是不是也是沒有虛部的實數?絕了,英語厲害了,可以轉移到對人的分析上,原來是有語言的基礎的。
苏格:是的,虚部,代表人的更广阔的潜能,可塑性,可能性,理想性,未来性。
拉图:見識了,我還以為就是概念的範疇的擴展,沒想到呀。
苏格:单向度的人,也就是点在直线上移动。直线,就像跑道,已经被规定好了。
拉图:人生的規劃,思考的維度,想像的界限,都是已經被無形規劃好了的人。
苏格:准确地说,是线段。
拉图:為什麼會有節點?還是說是分段的吗?
苏格:是的。教育的灌输,教化,就是要灌输给你这些,像打钢印一样。人生是有限的嘛。时间短,如线段。但是,人生不是线段,不是直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曲线,而是螺旋线。螺旋线的数学形式就是复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不断扩大的时钟表盘以垂直于自身圆心的方向做运动,其运动轨迹就是一种螺旋线。这比跑道更像是人生。
拉图:還可以這麼看的呀。果然把數學那一套用在數學領域裡面,還是小看了数学。
苏格:当然了,这是理想的人生模型了。没有人可以绝对达到,但可以无限逼近,而一个足以不断再产生“美好的个人”、“最可爱的人”和“爱的主体”的社会则是其必要条件。但大多数人却连朝这个方向、这种可能性想一下都不会,只顾着想在被规定的跑道上争一个名列前茅。
拉图:不過已經見識到了人還有這樣的可能性,那回去的話也很難了。
苏格: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由奢返俭难,由高阶生命返回低阶生命也难。注意一点,人年纪轻轻,就从复数变成实数的过程,就是在教育体制中血气被扼杀的过程。
拉图:哎,消磨時間和精力。最重要的是血氣還被扼殺了。多谢老师的赐教。
苏格:不客气。